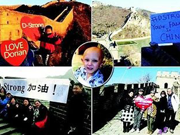毒土地上建學(xué)校,為了利益還是公益?
連日來,江蘇省常州外國(guó)語(yǔ)學(xué)校(以下稱常外)500名在校生疑似因化工廠污染地塊中毒一事引發(fā)社會(huì)廣泛關(guān)注。
常外8年級(jí)學(xué)生家長(zhǎng)張強(qiáng)(化名)已記不清這半年來有多少次與當(dāng)?shù)卣W(xué)校發(fā)生爭(zhēng)執(zhí),這樣的“拉鋸戰(zhàn)”讓眾多家長(zhǎng)筋疲力盡。

他一直不知道學(xué)校對(duì)面曾是化工廠。直到去年12月,學(xué)校里開始彌漫越來越濃的異味,隨后很多學(xué)生去醫(yī)院體檢,分別發(fā)現(xiàn)身體出現(xiàn)了問題。
張強(qiáng)發(fā)現(xiàn),從2013年學(xué)校開工到2015年8月學(xué)生入學(xué),學(xué)校對(duì)面的那塊“毒地”一直在修復(fù)中。家長(zhǎng)和學(xué)生質(zhì)疑,學(xué)校和政府部門在建校前都應(yīng)該知道對(duì)面是一塊尚未完成修復(fù)的“毒地”,但家長(zhǎng)和學(xué)生卻不知情。
4月18日傍晚,張強(qiáng)站在常外門口等女兒下課。他雙眼滿是血絲,談到這個(gè)話題很氣憤,反問道:“到底是孩子健康重要還是項(xiàng)目發(fā)展重要?”
環(huán)保部通報(bào)中的“毒地”
當(dāng)在電視上看到那幾個(gè)數(shù)字,張強(qiáng)驚呆了。
據(jù)央視報(bào)道,在一份常隆地塊項(xiàng)目環(huán)境影響報(bào)告上,這片地塊土壤、地下水里以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機(jī)污染物為主,萘、茚并芘等多環(huán)芳烴以及汞、鉛、鎘等重金屬污染物,普遍超標(biāo)嚴(yán)重。
其中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它在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濃度超標(biāo)達(dá)94799倍和78899倍,四氯化碳濃度超標(biāo)也有22699倍,其它的二氯苯、三氯甲烷、二甲苯總和高錳酸鹽指數(shù)超標(biāo)也有數(shù)千倍之多。
這塊面積26.2公頃的土地,在去年12月之前,張強(qiáng)一直以為是農(nóng)地,在政府的規(guī)劃里,這將是繁華的商場(chǎng)。他沒想到這里曾是3家農(nóng)藥化工廠,規(guī)模最大的江蘇常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jiǎn)稱“常隆化工”)建廠于1958年,使用該地塊長(zhǎng)達(dá)52年。
盡管常隆化工早在2011年就搬走了,但曾在常隆化工工作了30多年的退休員工胥建偉舉報(bào),常隆化工在搬遷過程中曾將大量危險(xiǎn)廢物埋于地下。
今年1月中旬,常外停課后不久,環(huán)保部華東督查中心會(huì)同江蘇省環(huán)保廳、常州市政府等組成調(diào)查組,到現(xiàn)場(chǎng)展開全面調(diào)查。他們也找來舉報(bào)人指認(rèn)“埋毒”地點(diǎn)。“在現(xiàn)場(chǎng)鉆了30多個(gè)孔,花費(fèi)了100多萬(wàn)元,花了近半個(gè)月,最后也沒有發(fā)現(xiàn)舉報(bào)所說的危廢,只有搬遷過程中不小心遺留在現(xiàn)場(chǎng)的兩小桶除草劑,總共只有30公斤。”常州市新北區(qū)環(huán)保局的一名負(fù)責(zé)人回應(yīng)。
胥建偉認(rèn)為,沒有找到填埋危廢的原因是環(huán)保局提供錯(cuò)誤圖紙。拆完了廠房的現(xiàn)場(chǎng)早已變成一塊荒地,沒有任何參照物。
但“毒地”還是存在的。今年1月29日,環(huán)保部公布了2015年12月人民群眾和新聞媒體反映的環(huán)境案件處理情況。其中,常隆化工被曝出在原廠址偷埋固廢。
環(huán)保部華東督查中心暗查發(fā)現(xiàn),常隆化工已拆遷完畢的常州農(nóng)藥廠原廠區(qū),挖掘出約1500土石方受污染土壤,南側(cè)正在進(jìn)行土壤修復(fù)作業(yè)。另外,常隆化工還被發(fā)現(xiàn)處理廢氣、廢液、廢渣的焚燒爐擅自停運(yùn)。
對(duì)此,常州市環(huán)保局委托上田環(huán)境修復(fù)股份有限公司對(duì)填埋區(qū)域進(jìn)行鉆孔勘察,現(xiàn)場(chǎng)挖掘出廢鐵桶(內(nèi)有少量黑褐色粘稠物)兩個(gè)、除草劑產(chǎn)品3包,共30公斤;含刺激性氣味的黑色淤質(zhì)土壤約1500立方米,另混有磚塊、水泥塊等建筑垃圾若干。
采樣后的樣本檢測(cè)結(jié)果顯示,主體成分為土壤,部分成分與建筑材料相似,部分有機(jī)物因子(總石油烴和4-氯甲苯)超標(biāo),其成分和常隆地塊內(nèi)其他土壤基本一致。
經(jīng)檢測(cè),土壤污染物系總石油烴和4-氯甲苯超標(biāo),前者是目前環(huán)境中廣泛存在的有機(jī)污染物之一。
同時(shí),環(huán)保部還表示,江蘇省環(huán)保廳督促當(dāng)?shù)卣涌煸瓘S區(qū)土壤修復(fù)進(jìn)度,妥善處置新發(fā)現(xiàn)的污染土壤,徹底消除環(huán)境隱患等。
4月18日,常隆化工原址上已砌起3米高的圍墻。圍墻內(nèi),一臺(tái)挖土機(jī)正在作業(yè),高土堆上種了樹。
未被認(rèn)同的土地修復(fù)計(jì)劃
公開信息顯示,2009年,常隆地塊3家化工企業(yè)完成搬遷,2011年完成拆遷平地。同年,當(dāng)?shù)丨h(huán)境部門調(diào)查后認(rèn)定:“根據(jù)場(chǎng)地調(diào)查和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結(jié)果,該地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用于商業(yè)開發(fā)的環(huán)境風(fēng)險(xiǎn)不可接受,必須對(duì)土壤和地下水實(shí)施修復(fù)。”
2013年,常州黑牡丹建設(shè)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jiǎn)稱“黑牡丹公司”)開始對(duì)污染場(chǎng)地開展土壤和修復(fù)工程。但該項(xiàng)目最終未達(dá)到預(yù)期目標(biāo)。
網(wǎng)上流傳著一份《三江口地塊土方開挖及樁基工程建設(shè)項(xiàng)目環(huán)境影響報(bào)告表》,日期顯示是2014年3月,編制單位為江蘇省環(huán)境保護(hù)廳,建設(shè)單位為黑牡丹公司。
從報(bào)告可知,常隆污染地塊包括三江口地塊,占地面積近14公頃,土方開挖和樁基建設(shè)施工周期原定為2014年4月~12月,項(xiàng)目投資7700萬(wàn)元。
據(jù)常州市新北區(qū)區(qū)域規(guī)劃圖,該地塊場(chǎng)地的土地利用性質(zhì)發(fā)生改變,調(diào)整為二類居住用地、綠化用地、市場(chǎng)用地和公共設(shè)施用地。
直到2014年3月,常州立項(xiàng)正式對(duì)常隆地塊進(jìn)行修復(fù),投資預(yù)算近4億元。
當(dāng)?shù)卣_始一輪修復(fù),但因刺激性異味太大,被迫暫停。據(jù)常外校長(zhǎng)曹慧介紹,早在2014年年底,常外隔壁的一所學(xué)校就有家長(zhǎng)曾向政府投訴“對(duì)面飄來異味”。
據(jù)常州環(huán)境科學(xué)研究院院長(zhǎng)徐圃青介紹,該工程主要針對(duì)商業(yè)用地功能進(jìn)行修復(fù),方法是將污染土壤挖出,再運(yùn)到水泥廠進(jìn)行異位修復(fù)。工程原定于2015年4月完工,但2014年水泥行情不好,導(dǎo)致原定修復(fù)工期嚴(yán)重拖后。
2015年12月,僅對(duì)3個(gè)重點(diǎn)污染區(qū)域進(jìn)行試挖,挖出的污染土壤暫存在堆場(chǎng)未運(yùn)走。也就是說,地下水修復(fù)工程當(dāng)時(shí)還未開展。
斷斷續(xù)續(xù)的修復(fù)工作以及濃烈的異味招致家長(zhǎng)抗議。1月15日,常州市新北區(qū)政府作出決定,將該地塊由商業(yè)開發(fā)調(diào)整為生態(tài)公園。
常州市政府通報(bào)稱,“鑒于常隆地塊周邊環(huán)境以及敏感目標(biāo)的變化”,原修復(fù)方案會(huì)對(duì)周邊敏感人群產(chǎn)生一定風(fēng)險(xiǎn),故此將土壤修復(fù)方案調(diào)整為覆土、綠化、讓污染物質(zhì)自然降解的方式,并將土地用途更換為綠化及公共設(shè)施用地,用生態(tài)公園取代了原計(jì)劃中的大型商場(chǎng)。
據(jù)介紹,1月15日修復(fù)方案調(diào)整為在受污染土壤上層覆蓋黏土,并不繼續(xù)清除地下的污染物質(zhì)。1月20日,調(diào)整后的修復(fù)方案通過專家評(píng)審,修復(fù)工程隨即再次啟動(dòng)。2月2日,現(xiàn)場(chǎng)施工完成。2月15日,工程通過驗(yàn)收。
修復(fù)方案的徹底改變卻讓家長(zhǎng)們質(zhì)疑。有專家表示,新修復(fù)方案里,黏土層的堆高需要充分的計(jì)算和論證,還要考慮地塊外的防護(hù)措施。從1月15日土地規(guī)劃用途更改到1月20日專家評(píng)審?fù)ㄟ^新方案,僅用時(shí)5天。
一位參與過土壤修復(fù)的企業(yè)人士介紹,土壤的修復(fù)涉及檢測(cè)、評(píng)估、設(shè)計(jì)、施工、監(jiān)理、驗(yàn)收等多個(gè)環(huán)節(jié)。目前,大家對(duì)土壤修復(fù)的了解還不夠,遇到污染嚴(yán)重、面積大的污染產(chǎn)地,甚至?xí)笤跇O短時(shí)間內(nèi)完成修復(fù)工作。
也有專家提出質(zhì)疑,覆土封蓋若要應(yīng)用于化工場(chǎng)地污染,只能作為一種臨時(shí)性處理方式。化工廠產(chǎn)生的污染土壤,其自然降解的能力很弱。如果沒有進(jìn)行隔斷處理,將來可能會(huì)造成新污染轉(zhuǎn)移,會(huì)給“毒地”附近居民區(qū)和學(xué)校帶來長(zhǎng)期威脅。
常州市政府回應(yīng)說,修復(fù)調(diào)整方案獲得國(guó)內(nèi)知名專家咨詢?cè)u(píng)估,并通過專家驗(yàn)收,目前,還將持續(xù)開展周邊敏感目標(biāo)的空氣、土壤和地下水監(jiān)測(cè)工作,“該地塊的生態(tài)隱患是可控的”。
為了利益,還是為了公益?
早在2013年,菲律賓SM集團(tuán)在常州市新北區(qū)龍虎塘鎮(zhèn)挑選了一塊19公頃的土地,要在這里建造一個(gè)大型購(gòu)物中心和城市住宅集為一體的商業(yè)綜合體。該地塊就包含在常隆地塊內(nèi)。
如果不發(fā)生這次風(fēng)波,也許這塊“毒地”順利轉(zhuǎn)型,且會(huì)成為房地產(chǎn)開發(fā)項(xiàng)目的“完美案例”。
從2008年開始,包括常州在內(nèi)的蘇南地區(qū)迎來一輪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作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和化工整治的重要時(shí)期,一大批老工業(yè)企業(yè)搬出城區(qū)。常州在全國(guó)率先開展了關(guān)停化工企業(yè)原廠址土壤污染調(diào)查,年內(nèi)完成首批35家關(guān)停化工企業(yè)原廠址土壤污染調(diào)查。
其中,常州化工廠地塊污染場(chǎng)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復(fù)工程處理污染土壤42萬(wàn)噸、地下水54萬(wàn)立方,創(chuàng)下“單個(gè)污染場(chǎng)地修復(fù)體量全國(guó)之最”。
2012年,常州市環(huán)保局在工作報(bào)告中提到,常州在江蘇省率先制定、實(shí)施了管理辦法和工作流程,國(guó)內(nèi)首創(chuàng)在土壤修復(fù)工程施工中引進(jìn)環(huán)境監(jiān)理,實(shí)施全過程嚴(yán)格監(jiān)管,而且在國(guó)內(nèi)率先全面開展關(guān)停化工企業(yè)原廠址土壤污染調(diào)查,常州市污染場(chǎng)地調(diào)查與修復(fù)工作已走出常州特色,形成“常州模式”。
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7月,常州市共完成了75家工業(yè)企業(yè)的遺留污染場(chǎng)地調(diào)查。
“毒地”修復(fù)似乎成為常州轉(zhuǎn)型的必經(jīng)之路
此次被推上風(fēng)口浪尖的常隆地塊正是常州市第二個(gè)實(shí)施土壤和地下水一體化修復(fù)的農(nóng)藥類污染場(chǎng)地修復(fù)項(xiàng)目。該項(xiàng)目還入選了環(huán)保部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fù)試點(diǎn)備選項(xiàng)目。
土地修復(fù)所要承擔(dān)的是高昂的修復(fù)成本。江蘇一家房地產(chǎn)公司董事長(zhǎng)劉剛(化名)介紹,這類“毒地”需要開發(fā)商承擔(dān)一定的土壤修復(fù)成本,轉(zhuǎn)讓價(jià)通常低于通過土壤修復(fù)工程驗(yàn)收的全凈土,這很大程度上可以緩解高昂的修復(fù)成本給財(cái)政帶來的壓力。
常州環(huán)境科學(xué)研究院院長(zhǎng)徐圃青表示,場(chǎng)地修復(fù)的價(jià)格很高,沒有資金平衡,地方政府不會(huì)去做這樣的項(xiàng)目。
新北區(qū)政府環(huán)保局一位官員稱,無論是之前的修復(fù)方案,還是目前變更土地使用用途后的修復(fù)方案,其成本一直都由政府承擔(dān),“具體數(shù)額我們不掌握”。
2012年,當(dāng)土地修復(fù)還在進(jìn)行時(shí),新北區(qū)就給常外發(fā)放了土地規(guī)劃許可證。第二年,常外順利拿到建設(shè)規(guī)劃許可證。這個(gè)可以容納2500人、投資3.1億元的新學(xué)校與“毒地”只有200米遠(yuǎn)。
這所2001年由江蘇省常州高級(jí)中學(xué)獨(dú)資創(chuàng)辦的私立學(xué)校,初中部每年的中考分?jǐn)?shù)和升學(xué)率在當(dāng)?shù)厥恰笆浊恢浮薄P∩鯎裥8?jìng)爭(zhēng)中,學(xué)校成為家長(zhǎng)“擠破腦袋”的選擇。在“毒地”風(fēng)波中,很多家長(zhǎng)遭遇現(xiàn)實(shí)尷尬,他們堅(jiān)持讓學(xué)校搬遷,而不是讓孩子退學(xué),“因?yàn)檎也坏礁玫膶W(xué)校了”。
常州市政府的解釋是,城市人口進(jìn)一步向常州高新區(qū)、產(chǎn)業(yè)園區(qū)集聚,新北區(qū)也急需更為豐富的教育資源;常州外國(guó)語(yǔ)學(xué)校的異地重建和搬遷,不僅可緩解交通壓力,也可大大提升北部新城教育的總體水平和綜合實(shí)力。
中科院生態(tài)環(huán)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黃錦樓說,在土壤修復(fù)問題上,國(guó)內(nèi)外最大的差距在于理念。國(guó)外重視調(diào)查、防控,不得已才去治理修復(fù),國(guó)內(nèi)仍停留在開挖、異位等快速修復(fù)上。而這些工作更多是出于房地產(chǎn)開發(fā)的需求。
如今,這個(gè)被推上風(fēng)口浪尖的項(xiàng)目,對(duì)常州相關(guān)政府部門來說變成了一個(g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jià)”的教訓(xùn):除了要承擔(dān)修復(fù)成本,還要放棄一項(xiàng)2.9億美元的投資,在利益和公益的選擇上可能也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 03-04
- 02-15
- 精彩必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