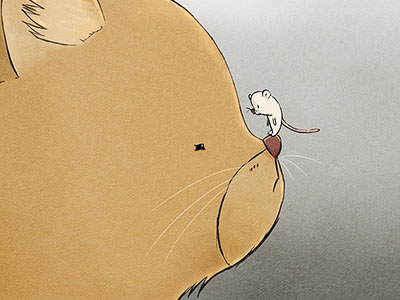吳一龍:夢(mèng)想辦一座為窮人免費(fèi)治腫瘤的醫(yī)院
今年是吳一龍的“豐收年”。
9月,在美國(guó)舉行的第16屆世界肺癌大會(huì)上,國(guó)際肺癌研究學(xué)會(huì)將“杰出科學(xué)獎(jiǎng)”頒給了吳一龍。這是該獎(jiǎng)40年來(lái)首次頒給華人科學(xué)家。頒獎(jiǎng)詞說(shuō):“吳一龍教授代表著肺癌研究歷史上的中國(guó)貢獻(xiàn),尤其是靶向治療為全世界樹(shù)立了榜樣,國(guó)際尤其亞太地區(qū)晚期肺癌治療原則、治療指南的證據(jù),絕大部分出自中國(guó)。”
而此前的8月份,中國(guó)臨床腫瘤學(xué)會(huì)在上海成立,吳一龍擔(dān)任第一屆理事長(zhǎng)。
豐收的喜悅,源自近30年的革新與沉淀。
這位59歲的中國(guó)肺癌治療領(lǐng)軍人物,致力于基因靶向藥物和精準(zhǔn)醫(yī)療的研究,證明了靶向藥物對(duì)東亞人種的特殊有效性,改變了全世界的肺癌治療指南。他希望,通過(guò)精準(zhǔn)醫(yī)療的發(fā)展,未來(lái)5―10年,讓肺癌可以像高血壓、糖尿病一樣,成為可控的慢性疾病。
人如其名。這個(gè)愛(ài)看古龍小說(shuō)的潮汕漢子,是廣東醫(yī)療界的“一條猛龍”。從當(dāng)年的“廣東肺癌第一刀”,到如今的“杰出科學(xué)家”,“刀客”霸氣已斂,胸中仍澎湃著救濟(jì)蒼生的“俠客夢(mèng)”。說(shuō)到動(dòng)情處,他的眼眸會(huì)閃過(guò)一絲孩童的純真、一寸刀鋒的銳利。
醫(yī)生除了有科學(xué)精神,還要有人文情懷
什么樣的人適合學(xué)醫(yī)?吳一龍列舉了三個(gè)標(biāo)準(zhǔn):博愛(ài),不內(nèi)向,有好奇心、不斷追問(wèn)。
他認(rèn)為,醫(yī)生除了有科學(xué)精神,還要有人文情懷。1988年他到德國(guó)留學(xué),有一天下午,跟著老師去聽(tīng)第二天的手術(shù)安排。醫(yī)生們穿著白大褂,筆挺站著。有兩位白頭發(fā)的人坐著,大家對(duì)他們很尊重,吳一龍判斷他們應(yīng)該是老教授。
開(kāi)始討論后,幻燈片顯示病人肺部情況,醫(yī)生們逐一發(fā)表意見(jiàn),老師進(jìn)行了總結(jié)。吳一龍以為那兩個(gè)“老教授”會(huì)做最后的陳述。誰(shuí)知他們說(shuō),“聽(tīng)你們說(shuō)了后,我知道了我的病情,知道了幾種治療方式,也知道了你們的態(tài)度和相應(yīng)的利弊”。
原來(lái)他們是病人!最后他們選擇了醫(yī)生推薦的治療方式。吳一龍深受震動(dòng),“原來(lái)醫(yī)生應(yīng)該這么當(dāng),科學(xué)嚴(yán)謹(jǐn)?shù)馗嬷尣∪顺浞钟凶饑?yán)地選擇、對(duì)待自己的生命。”后來(lái),對(duì)每一屆學(xué)生,他都會(huì)說(shuō)起這個(gè)例子。
醫(yī)生永遠(yuǎn)需要學(xué)習(xí),吳一龍?bào)w會(huì)特別深。他1990年回國(guó)后,整整3年都在整理病歷。苦悶之時(shí),他看到一篇英國(guó)文獻(xiàn),針對(duì)過(guò)去30多年的肺癌治療進(jìn)行總結(jié),采用的研究方法叫做“個(gè)人資料的綜合分析”,文獻(xiàn)中的森林圖也看不懂。而且,文獻(xiàn)結(jié)論非常嚇人:做完手術(shù)再加一個(gè)通常認(rèn)為是保險(xiǎn)的放射治療,沒(méi)帶來(lái)好處,反而使死亡率提高了21%,“我就想弄清楚他們是通過(guò)什么方法得出這個(gè)結(jié)論”。
他就寫(xiě)信向德國(guó)的老師請(qǐng)教。老師回信解釋說(shuō),過(guò)去的研究只是依據(jù)少數(shù)病人的個(gè)人資料得出結(jié)論,這種新的研究方法是把所有病人的數(shù)據(jù)都納入數(shù)據(jù)庫(kù)中進(jìn)行計(jì)算。森林圖的每一條線就代表一個(gè)研究群體,研究對(duì)象越多,結(jié)論越可信。
“這就是循證醫(yī)學(xué)的研究方法。循證醫(yī)學(xué)是遵循證據(jù)的醫(yī)學(xué),必須依據(jù)大量的病人情況。我們之前做手術(shù)大多依據(jù)經(jīng)驗(yàn),現(xiàn)在看往往是錯(cuò)的。”吳一龍從此萌發(fā)了對(duì)循證醫(yī)學(xué)的興趣,花了2年學(xué)習(xí)、“弄懂”這個(gè)問(wèn)題。
1998年,吳一龍?jiān)谥袊?guó)第一次開(kāi)講循證醫(yī)學(xué)這門課,轟動(dòng)一時(shí)。2000年,他開(kāi)辦了循證醫(yī)學(xué)雜志,在中國(guó)推廣循證醫(yī)學(xué),現(xiàn)在已被醫(yī)學(xué)界普遍接受。
要有“銳氣”,不斷追求新知識(shí)
上海一位老教授曾形容,吳一龍有三氣:霸氣、銳氣、義氣。
“霸氣”,是指吳一龍講出一個(gè)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很少人能夠反駁,在無(wú)形之中就有一種霸氣。吳一龍覺(jué)得這跟他在德國(guó)的經(jīng)歷相關(guān),訓(xùn)練出了講證據(jù)的嚴(yán)謹(jǐn)思維方法,“把證據(jù)擺出來(lái),就沒(méi)人能夠反駁”。
“銳氣”,因?yàn)樗麑?duì)新的知識(shí)點(diǎn)很敏感,能夠馬上意識(shí)到新事物的重要性。比如說(shuō),奧巴馬去年大力提倡的精準(zhǔn)醫(yī)學(xué),早在2000年的時(shí)候,吳一龍就已經(jīng)開(kāi)始關(guān)注這個(gè)領(lǐng)域。
吳一龍的“義氣”是出了名的,他說(shuō)自己是典型的潮汕人,“除了盡心幫助別人,當(dāng)其他人還模棱兩可的時(shí)候,我會(huì)把事實(shí)的真相說(shuō)出來(lái)”。
有一年,湖北的一位高干在北京就診,也請(qǐng)了吳一龍會(huì)診。在座的專家均診斷患者得了肺癌,但從影像學(xué)資料和臨床表現(xiàn),吳一龍覺(jué)得病人患的并不是肺癌。“我不好直說(shuō),就巧妙地繞一個(gè)圈子來(lái)表述我的想法。最后病人在我這里治療,到現(xiàn)在10年了,他還活得好好的”。
吳一龍認(rèn)為,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真正的“大醫(yī)”會(huì)追求最高層面的自我實(shí)現(xiàn)、心理滿足,對(duì)物質(zhì)方面沒(méi)有太高的要求。有民營(yíng)醫(yī)院請(qǐng)他,開(kāi)出300萬(wàn)元年薪。但他認(rèn)為,自己更想要做研究、探索未知,“如果不能滿足這一層面的需求,300萬(wàn)還不如30萬(wàn)”。
整合社會(huì)資源惠及更多病人
“讓肺癌成為慢性病”,是吳一龍致力的方向。他針對(duì)一系列基因突變進(jìn)行深入研究,率先發(fā)現(xiàn)了中國(guó)人身上特有的肺癌驅(qū)動(dòng)基因有別于西方人,證明了靶向藥物“易瑞沙”對(duì)東亞人種的特殊有效性,讓患者中位生存期延長(zhǎng)3年多,改變了全世界的肺癌治療指南。
靶向藥物有一個(gè)致命弱點(diǎn):昂貴。以一代藥物易瑞沙為例,一名肺癌病人一個(gè)月用藥費(fèi)用高達(dá)1.5萬(wàn)元。“為什么這項(xiàng)讓全球肺癌患者獲益的成果,卻因藥費(fèi)高昂,讓國(guó)內(nèi)很多患者望而卻步?”吳一龍做了件與醫(yī)生本職無(wú)關(guān)的工作,與廣州市醫(yī)保局協(xié)商了整整兩年。為了能得到認(rèn)可,他甚至幫政府設(shè)計(jì)了醫(yī)保結(jié)算的后臺(tái)。終于在2010年促成價(jià)格不菲的“易瑞沙”和“特羅凱”這兩種肺癌靶向藥物納入廣州醫(yī)保,肺癌病人每月自付1000―2000元就能吃上救命藥。這在全國(guó)還是第一次。
今年8月,中國(guó)臨床腫瘤學(xué)會(huì)在上海成立,吳一龍擔(dān)任第一屆理事長(zhǎng)。他希望自己在任期內(nèi)能完成兩件事:第一,不再照搬歐美的做法,起草一部符合中國(guó)國(guó)情的治療腫瘤的指南;第二,培訓(xùn)更多的腫瘤醫(yī)生,“讓腫瘤醫(yī)生都能把老百姓的病治好,而不是來(lái)到我這里才能治好,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吳一龍?”
吳一龍夢(mèng)想中的醫(yī)院,是可以整合利用慈善捐贈(zèng)、新藥研發(fā)等各種社會(huì)資源,為窮人免費(fèi)治療腫瘤等大病。可以讓病人接受先進(jìn)的臨床試驗(yàn),器械、藥物和治療都是最好的。“病人不是小白鼠,精準(zhǔn)醫(yī)療成功的可能性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失敗。如果病人是有錢人,可以捐款給醫(yī)院,造福其他患者”。
去年,法國(guó)的朋友帶著吳一龍去參觀當(dāng)?shù)匾凰t(yī)院。除了見(jiàn)識(shí)到全法國(guó)最新的藥物和設(shè)備外,他特別注意到,一些大藥廠都在醫(yī)院附近設(shè)立了研發(fā)部門,研究成果可以立即應(yīng)用。“這種醫(yī)院可以利用社會(huì)上所有資源,來(lái)解決一般老百姓的問(wèn)題。這樣的醫(yī)院,我干起來(lái)就有力量。”吳一龍說(shuō),這個(gè)夢(mèng)想并非遙不可及,希望有一天能實(shí)現(xiàn)。
他感慨地說(shuō):“一個(gè)人的力量有限,真正的大醫(yī)不是一天多看幾個(gè)病人,而要整合所有的社會(huì)資源,惠及更多的病人。現(xiàn)在越來(lái)越覺(jué)得,一輩子,能做一兩件對(duì)民眾有益的事情,就很滿足了。”
- 精彩必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