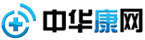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在城市實施“一對夫婦一個孩”政策后出生的一代,隨著時間的流逝,不可避免地長大、成人,直至開始擔負起社會賦予他們的責任并承擔應盡的義務。
在今天的中國,有很多“第一代”獨生子女,雖已成年的他們仍習慣著上一代的照顧,卻已不得不開始面對自己的下一代。而他們的下一代卻與他們一樣,背負著相同的特殊身份:獨生子女。
兩代獨生子女,帶著各自區別于任何一個時期中國人的長處和弱點,在21世紀初的當代終于相遇了。這是一幅有意思又特別的圖景。
他竟然認不出哪個是自己的孩子
生于1979年的陳銘,大學畢業后在上海一家IT公司做程序員,而妻子、1981年出生的方嵐是他的師妹,前年考上了公務員,在區檔案局工作。雖然在大學時就談起了戀愛,但他們常說自己在沒想結婚的時候結了婚,在沒想生孩子的時候生了孩子。用陳銘的話來說,是“父母覺得是時候了”。
雖然做了爸爸,但陳銘卻說“沒什么感覺”,因為自己的生活沒太大變化。每天下班回來,照舊吃父母已經準備好了的熱菜熱飯,吃完了就去上網打游戲。方嵐也是獨生女,家務幾乎不太會干,吃完飯,要么看看電視看看碟,要么上網聊聊天。
“說實話,孩子怎么帶,我們一點也不會。”小夫妻倆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還是挺理直氣壯的,“反正父母早就說了,有了孩子他們幫著帶。我們也想趁父母身體好、帶得動孩子的時候,早點生了算了。”
其實陳銘和方嵐像任何一個初為人父人母的夫妻一樣,曾憧憬和想象過怎么養育好孩子,但最后他們還是放棄了。
“小孩好玩是蠻好玩的,可實在是太麻煩!晚上一哭,你就要起來哄,尿布濕了,你就要起來換。熱了冷了餓了飽了都要鬧,太累了!”陳銘夫婦向很多人抱怨過孩子出生后的操勞,并說他們已無法忍受了。因為煩躁,陳銘還動手打過還是嬰兒的女兒。
“也不能怪他們,家家都只有這么一個孩子,哪家不是從小寵著慣著,也就別提做什么家務帶孩子了。哪像我們小時候,妹妹是姐姐帶大的,家務是兄弟姐妹分著做的。”作為孩子奶奶的毛阿姨多少有些無奈的說,“現在再讓他們學這些,不太可能了。”
但目前毛阿姨最擔心的還不是兒子兒媳能不能學會照顧好自己的孩子,而是他們對自己的孩子有某種陌生感。
毛阿姨說起一件小事,有個周末她和陳銘一起帶孫女去醫院做例行檢查。她在醫生檢查的空當上了趟衛生間,而陳銘則坐在檢查室外打著掌上游戲機等候。回來的時候,毛阿姨遠遠聽見醫生喊讓家長進去把孩子抱走。待她走進門內,卻看見陳銘呆呆地看著床上并排的三個孩子——原來他竟然認不出哪個是自己的孩子。
“其他時候也是,親戚朋友來看望孩子時,他就站在那里,轉眼又打游戲了,好像跟他一點關系都沒有。”毛阿姨深深嘆了口氣,身邊一歲不到的小孫女緊緊貼著她,誰抱都不肯。“我有時候還真有點害怕,兒子是我一手培養的,現在孫女看起來也要我一手帶大,等孫女再大點,他們父女會是種什么感情呢?”
雖然做了爸爸,但陳銘卻說“沒什么感覺”,因為自己的生活沒太大變化。
其實陳銘和方嵐像任何一個初為人父人母的夫妻一樣,曾憧憬和想象過怎么養育好孩子,但最后他們還是放棄了。
毛阿姨有時也會反省,是不是因為自己這一代失去太多,所以才把太多照顧和希望給予了兒子一代,以至于擁有太多的他們對下一代沒有了需要?“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比起尚且對下一代到來還無知無覺的陳銘,1979年出生的柴曉怡雖然還沒結婚生子,卻已提前遇上一群小小的孩子。身為幼兒老師她,談起一些孩子,就是兩個字——頭疼。
柴曉怡在上海博山東路上一家幼兒園工作快五年了,也算得上有經驗的了,但她的經驗不全是把孩子怎么教得品學兼優,還包括如何對他們“用強”。
| 豐胸 保濕 美白 防曬 抗皺 控油 除痘 祛斑 |
|